 然而,中國的讀書人,最高的理想是做福國家、做福人群。「儒,人之需也」,就是社會所需要的一群。正如宋代大儒張載張橫渠先生所說,讀書人要:「為天地立心,為生民立命;為往聖繼絕學,為萬世開太平。」這個,我贊成。但是書讀得越多,越自覺無知。我是那種無論看什麼書,都會興奮莫名,不止全盤受落,還要四出宣傳的人。就算讀過李天命 (1993),卻仍然養不成那種獨立思考能力,毫無批判的精神。例如當我看完《李光耀回憶錄》(李光耀,1998/2001) 時,我是十分欣賞他的,尤其他那「有中國特式的費邊主義 (Fabian)」。正所謂「衣食足」,然後才能「知榮辱」;而他真的就在夾縫中養活了新加坡。然而,當我看到在新加坡牛車水門外的「演說者角落」(Speaker's Corner; New Straits Times, 2000),只有寥寥三、五個老人在和旁邊地盤的噪音比音量,我才知道,這個成功地讓新加坡度過赤化危機的制度,也有它的缺點。但是最能描述我這種人的,竟是革命性地發展出進化論的達爾文 (Charles Darwin)。在他的自傳 (Darwin, 1958) 裏,他說自己:
然而,中國的讀書人,最高的理想是做福國家、做福人群。「儒,人之需也」,就是社會所需要的一群。正如宋代大儒張載張橫渠先生所說,讀書人要:「為天地立心,為生民立命;為往聖繼絕學,為萬世開太平。」這個,我贊成。但是書讀得越多,越自覺無知。我是那種無論看什麼書,都會興奮莫名,不止全盤受落,還要四出宣傳的人。就算讀過李天命 (1993),卻仍然養不成那種獨立思考能力,毫無批判的精神。例如當我看完《李光耀回憶錄》(李光耀,1998/2001) 時,我是十分欣賞他的,尤其他那「有中國特式的費邊主義 (Fabian)」。正所謂「衣食足」,然後才能「知榮辱」;而他真的就在夾縫中養活了新加坡。然而,當我看到在新加坡牛車水門外的「演說者角落」(Speaker's Corner; New Straits Times, 2000),只有寥寥三、五個老人在和旁邊地盤的噪音比音量,我才知道,這個成功地讓新加坡度過赤化危機的制度,也有它的缺點。但是最能描述我這種人的,竟是革命性地發展出進化論的達爾文 (Charles Darwin)。在他的自傳 (Darwin, 1958) 裏,他說自己: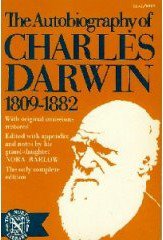 I have no great quickness of apprehension or wit which is so remarkable in some clever men, for instance, Huxley. I am therefore a poor critic: a paper or book, when first read, generally excites my admiration, and it is only after considerable reflection that I perceive the weak points. My power to follow a long and purely abstract train of thought is very limited; and therefore I could never have succeeded with metaphysics or mathematics. My memory is extensive, yet hazy: it suffices to make me cautious by vaguely telling me that I have observed or read something opposed to the conclusion which I am drawing, or on the other hand in favour of it; and after a time I can generally recollect where to search for my authority. So poor in one sense is my memory, that I have never been able to remember for more than a few days a single date or a line of poetry.
I have no great quickness of apprehension or wit which is so remarkable in some clever men, for instance, Huxley. I am therefore a poor critic: a paper or book, when first read, generally excites my admiration, and it is only after considerable reflection that I perceive the weak points. My power to follow a long and purely abstract train of thought is very limited; and therefore I could never have succeeded with metaphysics or mathematics. My memory is extensive, yet hazy: it suffices to make me cautious by vaguely telling me that I have observed or read something opposed to the conclusion which I am drawing, or on the other hand in favour of it; and after a time I can generally recollect where to search for my authority. So poor in one sense is my memory, that I have never been able to remember for more than a few days a single date or a line of poetry.且讓我試譯如下:「我 (達爾文) 並不是一個很聰穎的人,因此亦是一個很差的評論家:任何論文或書籍,我只要一看便會很興奮與讚嘆;之後需要經過相當的時間我才會想到它的弱點。以我有限的腦筋,實在跟不上人家一大串的抽象思想。所以我永不能成為 (形而上的) 哲學家或數學家。我的記憶力不算差,雖然有點模糊,但是足夠叫我想起其他人曾提出的正反論點。有需要的時候,我還是能找到那些參考來支持我的論點。從某角度來說,我的記憶力卻又不算太好,我總是不能把那些特別日子或浪漫詩句記牢多幾天。」
 眾所周知,論語記載的是孔子生前教學的講話,由學生編纂成書。由於竹簡珍貴,只有很少句是重覆的。而我記得重覆了的兩句,是他對「巧言令色」的批評(學而第一、公冶長第五、衛靈公第十五) 以及「不在其位,不謀其政」(泰伯第八、憲問第十四)。為什麼孔子那麼反感呢?本著「經史合參」的精神,可知是與那時的社會風氣有關。當時的「清廉之士」,好像齊國的陳文子,對社會不滿,只管在野批評,最後移民他方,卻未能真的對社會有所貢獻;孔子說他:「清矣。未知,焉得仁」;對獨善其身的荷蓧丈人,子路亦說:「不仕無義……欲潔其身,而亂大倫,君子之仕也,行其義也。道之不行,已知之矣!」(微子第十八)。儒家認為,如果你要為民請命,你便最好走進建制裏;就是這個「不仕無義」,叫他們明知「道之不行」,仍「知其不可而為之」(憲問第十四)。
眾所周知,論語記載的是孔子生前教學的講話,由學生編纂成書。由於竹簡珍貴,只有很少句是重覆的。而我記得重覆了的兩句,是他對「巧言令色」的批評(學而第一、公冶長第五、衛靈公第十五) 以及「不在其位,不謀其政」(泰伯第八、憲問第十四)。為什麼孔子那麼反感呢?本著「經史合參」的精神,可知是與那時的社會風氣有關。當時的「清廉之士」,好像齊國的陳文子,對社會不滿,只管在野批評,最後移民他方,卻未能真的對社會有所貢獻;孔子說他:「清矣。未知,焉得仁」;對獨善其身的荷蓧丈人,子路亦說:「不仕無義……欲潔其身,而亂大倫,君子之仕也,行其義也。道之不行,已知之矣!」(微子第十八)。儒家認為,如果你要為民請命,你便最好走進建制裏;就是這個「不仕無義」,叫他們明知「道之不行」,仍「知其不可而為之」(憲問第十四)。為什麼「不在其位,不謀其政」那麼重要呢?我最敬佩的南懷瑾老師 (2003) 曾說:「你我所知道的情報、資料,都是從報上看來的,並不是第一手資料,可靠性大有問題。就算是可靠的,在報紙上發表出來的,還是有限,不知道還有多少不能發表的,而且和此刻的現況,又相隔很遙遠了。像這樣如何可以去談政治?而且政治絕對要靠經驗,不是光憑理論的。你說某某不行,你自己來試試看,毫無經驗的話,不到三個月就完了」其實,孔子做司寇,也是做了三個月就完了。反而,最多人咒罵的、表面毫無「骨氣」的人,好像南北朝的馮道、甚至漢奸如汪精衛等,卻以他們的「圓滑」,為當時動亂社會中的人民提供了一個喘息的機會。
在解釋「博學而篤志」(子張第十九) 時,他再說:「對人,學問並不一定可貴,但是文人有知識,最喜歡亂叫。我們幾十年來,社會亂成這個樣子,首先鬧的還不是一般不成器的知識分子。借題發揮來鬧,對某一人不滿意,就借題發揮的鬧,結果把一個國家鬧成這個樣子……這就是博學不一定有用,博學要篤志,有一個中心,意志堅定,建立人品,那麼知識淵博,有如一顆好的種子,意志的堅定是肥料,培養出花和果來。內在沒有一個中心,知識越淵博,思想越危險,覺得樣樣都有道理,容易動搖,應該是真理只有一個,要把它找出來,所以要篤志」;在解釋秦始皇坑儒時,他叫我們「注意歷史上『處士橫議』四個字。秦始皇最初找好多高級知識分子開會,提出很多問題向他們請教,開會時,大家屁都不放一個,開完會以後,心裡又在嘀咕。這還不算頂討厭,更討厭的是那些沒有做到官的處士們,又生橫議,雞蛋裡去挑骨頭,蠻橫地找道理,又不是走直道,所以秦始皇一氣就坑了這些人。」
 因此,對韓非子所說:「儒以文亂法,而俠以武犯禁」,南老師解釋道:「韓非子的理由是儒者知識多,嘴會說,手會寫,有許多意見提出來,思想不同,使法令不能推行,難於執法。」那南老師是否反對知識份子參政?非也。他語重心長地不斷重覆:「一個知識分子,學問並不是文章,是作人做事。作人做事成功還不算,還要把自己的學問,用出來立人,有利於國家、社會、天下」。他自己便曾經投筆從戎,在抗日戰爭中屯兵戍邊;雖然精於佛、道之說,甚至成為藏密的大師,卻仍然心存救世的胸懷,孜孜不倦地在世界各地宣揚中國文化,為的,正是「為往聖繼絕學,為萬世開太平」。他常說:亡國不可怕,失去了文化的根才可怕;一個有根的民族,好像猶太人,亡國可以再復;一個無根的民族,好像印度人,獨立了還是在模仿其他人:以前是亞利安人、蒙古人,現在則是模仿英國人 (Naipaul, 2002)。
因此,對韓非子所說:「儒以文亂法,而俠以武犯禁」,南老師解釋道:「韓非子的理由是儒者知識多,嘴會說,手會寫,有許多意見提出來,思想不同,使法令不能推行,難於執法。」那南老師是否反對知識份子參政?非也。他語重心長地不斷重覆:「一個知識分子,學問並不是文章,是作人做事。作人做事成功還不算,還要把自己的學問,用出來立人,有利於國家、社會、天下」。他自己便曾經投筆從戎,在抗日戰爭中屯兵戍邊;雖然精於佛、道之說,甚至成為藏密的大師,卻仍然心存救世的胸懷,孜孜不倦地在世界各地宣揚中國文化,為的,正是「為往聖繼絕學,為萬世開太平」。他常說:亡國不可怕,失去了文化的根才可怕;一個有根的民族,好像猶太人,亡國可以再復;一個無根的民族,好像印度人,獨立了還是在模仿其他人:以前是亞利安人、蒙古人,現在則是模仿英國人 (Naipaul, 2002)。我自問沒有「兼善天下」的氣魄和能力,但又不敢「獨善其身」,愧對教我育我的先賢往聖,惟有以「立人」為目標,希望有一天能「得天下之英才而作育之」,由教育下一代的內心去開始改變社會。說到底,每一個政治理想的失敗,都源於人民素質太差、精神教育不足。有誰能說共產主義存心不良?它的精神和《禮記》的「大同」本是一樣的。相反地,民主制度亦會選出野心家、獨裁者、甚至白痴,亦能做成「大多數的暴政」(Tyranny of Majority; Mill, 1859);除非人民受過真正的「教育」(不是我們現在的那些「職業訓練」),眼睛變得雪亮,人人心中以全人類的幸福為目標,不再流於偏狹的民族沙文主義、宗教原教旨思想、無止境的經濟侵略、擴張與對環境的剝削,那就是人類之福了。
最近很多人爭論陳日君主教應否干預香港的政治。說來好笑,作為一個天主教徒,我曾經是「正義和平委員會」旗下「關社組」的第一批成員。當時我們的領袖是在美國讀過社會學項士的陳滿鴻神父。一方面我贊成教徒是社會的良心,對不公義要作出回應;一方面我又怕愚民對教會的盲目信任會成為野心家的工具,最後重演中世紀的歷史。所以,我最後轉了到「培育組」,以貫徹我「教育第一」的思想,還因此和陳日君主教開過會呢。後來,我還是因為不願教聖經以外的東西 (就是那些教會的教條與禮儀) 而沒有再教了。到了今天,如果你想知道教會的「政見」,你還是可以到慈雲山聖文德堂去聽陳滿鴻神父講道,或者到伍華書院裏的善導之母堂聽聽勞工階層的聲音。
Reference:
Darwin, C. (1958) & Barlow, N. (Ed., 1993). Written May 1st, 1881 (ch. 7, para. 13). The Autobiography of Charles Darwin 1809-1882. W. W. Norton. Retrieved from http://www.amazon.com/gp/product/0393310698; see also http://www.gutenberg.org/dirs/etext99/adrwn10.txt
Naipaul, V. S. (2002). An Area of Darkness. Vintage. Retrieved from http://www.amazon.com/gp/product/0375708359
New Straits Times (2000, September 24). Singapore's Speaker's Corner. Retrieved from http://www.sfdonline.org/Link%20Pages/Link%20Folders/Political%20Freedom/nst1.html
Mill, John Stuart. (1859). On Liberty. Retrieved from http://en.wikisource.org/wiki/On_Liberty; see also http://en.wikipedia.org/wiki/On_Liberty
李天命 (1993),李天命的思考藝術,允晨文化。載於 http://www.books.com.tw/exep/prod/booksfile.php?item=0010019177
李光耀 (1998),李光耀回憶錄:風雨獨立路,外文出版社
李光耀 (2001),李光耀回憶錄:經濟騰飛路,外文出版社
南懷瑾 (2003),南懷瑾選集.論語別裁,復旦大學出版社。載於 http://www.books.com.tw/exep/prod/booksfile.php?item=0010281511
1 則留言:
我跟你一樣,不愛談論政治。首先是因為我不懂,其次是我認為政見和宗教都是主觀喜好,沒什麼好討論。上星期我認識了一位朋友,他只擁護滿清政府;我自己嘛,就傾向周朝封建制度。遇上我們此等瘋子,還有什麼好說呢?
在今日的社會,越標榜道德/理性的政客其實越無恥/無知。例如最講道德的民主派,撒謊撒得最狠:124 的250,000? 去年的530,000? 由低級騙子和政棍隨機組織的「騎劫民主運動」可以引領香港人去哪裡呢? 關於遊行人數的討論,可看看這個blog:
http://www.zonaeuropa.com/20051206_2.htm
民主派是什麼人,讀畢可以舉一反三。
發佈留言